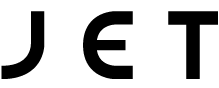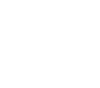芝姐災難大全 | 卓韻芝專訪 出封律師信吿自己
2024-05-26

中三入商台做DJ,有人認識芝see菇bi,有人認識卓韻芝:有人睇她長大,有人睇住她長大,但因為她早入行,其實更多人是睇她長大同時睇住她長大。她好似全香港人都共同擁有的一個中學同學,讀書很叻同時很好玩,會給你介紹好多好東西。小時候經她文字早早知道世界有Leonard Cohen、Raymond Carver、 Herzog等勁人,會自覺比其他同學酷一點,多少有些曲高和寡的沾沾自喜。
曾共渡過漫長的歲月,某日她做回卓韻芝,勤力得像頭牛,強得天堂也不收她。懷疑她每日都有100小時用,寫書寫劇本拍電影,那工作簡歷似活了幾輩子;又懷疑她比牛還多四個胃,專門用來消化一切文字與知識;又羨慕她的口齒伶俐,同時也怕被她的詞鋒拮傷。再後來,一度以為沒有男人敢娶才女,但前幾年她結婚了,過了一段日子後又離婚了。
今年阿芝45歲,她說現在是她活得快樂的時候,開了新的品牌、新的戲、新的獨腳戲;然此時回望十幾歲的自己,她沒有意想中的多愁善感,而是怒哮一句:「我要給她發律師信!」
text. yui
photo. Kit Chan
wardrobe . Christopher Esber、 Junya Watanabe @JOYCE hair . Marvin@shhh_group
venue. Little Tai Hang

出一封律師信吿她
如果人平均都能夠活到90歲,阿芝目前正處於整個這輩子的正中央。座標正處於赤道,是熱帶雨林的氣候,有點熱,但充滿生命力;種甚麼就生長甚麼,是一個生命的invincible summer。她甚至覺得一生以往從未像現在般活得清清楚楚、快快樂樂,對未來保持一種渴的狀態。「我跟自己下定決心了,要不就改變,要不就同一個人走進墳墓。」自從萌生這個念頭,她開始每天都期待著自己的下半生怎麼樣過。那天她在夜冷舖挖寶,找到了一本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精裝版的,居然只值港幣20元,好慘。把書救回家,讀下去她赫然發現,蘇軾因烏台詩案被眨變成東坡居士,在黄州寫《前赤壁賦》的時候,也是45歲。「作為一個都市人,40幾歲應該是生命綻放得很美,而大家都可以握緊自己生命中最美的時刻。」
成名趁早,阿芝未夠30歲已經被冠上才女的大名,做過DJ主持作家導演編劇監製。但現在她回想,20幾歲她面對兩道拉力,一面是面向世界的恐懼與自我批判,一面是自我價值的認同,兩邊不斷將自己扯開,那種內耗幾乎是宿命性地發生;30幾歲的她貌似比較知道自己是甚麼,向著標竿直跑,但內耗通常在途中發生,到頭來發現原本設定的那個目標不是自己最想要的。「之後演出的那場獨腳戲,其中有一部份我要和20幾歲的自己對話,是剛剛學會開車的自己。」她大笑指:「我常說,如果要寫封信給20歲的自己,我會出一封律師信給她,因為她開車太慢了,後面架車好危險。」

女人對痛感有點遲
今年二月,阿芝建立了自己品牌「WEMAN」。她發現許多人身心都不健康,許多人都在夜裡無法好好入眠,她自己也深受失眠之苦。後來她讀神經科學,讀了不少書。「我不懂New Age也不懂Spiritual,我只是喜歡神經科學。」深入了解後,她驚訝神經科學在西方明明已盛行幾十年,但在香港卻無人關注。她又嘗試許多諸如TRE (壓力釋放運動)、動態呼吸、冥想、吶喊治療等方法,詫異原來解決身心問題居然簡單如食生菜。因此她建立了「WEMAN」,去分享那些知識與資訊,主動改變世界。「例如動態呼吸,我們會從呼吸中得到好多個直覺,從身體存庫中得出某些答案,而那些答案是很清晰。即是說,你會求助於一種所謂的mental clarity,即腦袋的清晰度。不是依靠你的前額葉去思考,而是去問下你自己整個guts。因為由你出世開始,每一個記憶都其實都儲存在你的身體裡頭。你的前額葉不會記得你4歲暑假第一日做過甚麼,但你的身體會記得。」阿芝舉例,別人常辯稱自己是resting bitch face(天生臭臉綜合症),但在神經科學這件事並不成立,學者曾經研究面癱患者與他們的內在情緒,發現臉部肌肉和內在情緒是對等的。「你的肌肉就好像一個塑膠模型,而那些負面想法與狀態就是曲奇麵團,很坦白的,倒模出來就是那個樣子。所以別人常說有自信就會靚那些說辭,其實半點也不虛。所以如果呆著沒事幹,也最好想些開心事情,你微笑的表情會被臉部肌肉紀錄下來。」
阿芝說,「WEMAN」起初打算著眼女性社群,沒想到後來也有不少男性都感興趣。她受訪時曾經說過,社會對男女的差別待遇仍存在,會發現好多人抱著「男人代表全人類說話,女人代表女人說話」的古板想法。做過無數個訪問,她最厭煩的一種問題是:「你是不是女權主義者呀?」性別議題確實是當代最燙手的事物之一,沒有人能夠得到半個理直氣壯。談女權男權人權,怎一個煩字了得。倒不如說說女人,英劇《Fleabag》裡頭有這樣的一個形容,說女性生來就有疼痛,經痛、胸痛、分娩;男人不會,但他們自己找疼痛,用運動、打鬥、戰爭。「女性同痛楚是好friend的,我們常常見面。痛是一種sensation,但未必是女性的perception。」他認為女人對痛楚有鈍感:「由於經常痛,痛到我們對痛的感覺有點遲。當一件事經常發生在你身上,你就會失去敏鋭。

滑手機實在太昂貴
與阿芝見面當日,她拿著最新一期《The New Yorker》浩浩蕩蕩過來。有人問這本書是不是拍攝道具,她差點要翻個大白眼:「咩呀,我真的睇緊!」智慧手機時代下,阿芝的生活尚未算過份數碼化,最近她看完三宅唱的《惠子的凝視》,被電影中的菲林質感打動,非常嚮往拍一部16釐米菲林電影。「現在我們手機能看到海量的內容,都是畫面質素好低的東西,手機這樣『fat fat』下,人們居然就看了半天。」阿芝坦言自己極少看社交平台的東西:「死啦,我覺得如果坦白答會死㗎。」但還是真誠回答:「大家都看,我就做些好內容給大家看,我是好坦誠好主動跟大家溝通的。但滑手機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件太昂貴的事情了,真的很昂貴。滑一小時手機,那些時間已經夠我改好一稿劇本。」滑手機常常帶給阿芝的只有空虛感。「時間這東西,每個人都有,但幾乎全部人都浪費它。其實人有時候不需要太叻,不需要十分有遠見,你只需要善用個時間就已經跑贏別人半條街。」哦,上天原來是公平的,阿芝一日也沒有100小時,只是她很珍惜去用。
那阿芝是怎麼樣使用時間的呢?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基本上毫無章法可言,可能今天是早上5點睡、明天又晚上8點睡;後天是淩晨3點睡,大後天又晚上12點睡,作息毫不定時。只有外婆是她生活唯一的錨,不論在忙甚麼,她都會盡量6點坐定定陪她吃晚飯。開始一天之前,她會先決定當日要做甚麼事,大概定下是上晝做還是下晝做,再在那些時附近的時間前攝後攝,盡量利用。不過有趣的是,她嚴格遵守每做一件事都不會超過四個小時,哪怕對白寫到一半、電郵打到一半,鐘一響就必須要sharp cut,無情講。而且在同一日裡,她不會整天只做一件事,也絕不會連續8小時做同一件事。「這是經歷長時間實驗得出的結果,如果超過4小時做同一件事,就會開始打圈。包括那些有長時間寫作經歷的作家也是這樣的,如村上春樹,他不會連續工作這麼久,因為那個專注的能量是有限度的。」夠鐘,阿芝就會很想出去走走。她試過無端從家裡步行到北角買花;又有試過走去銅鑼灣的書店看英文書目錄,但沒有打算買任何的書;反正,就是做些毫無目的的事情。

婚姻就是結拜兄弟
春天一個早上,阿芝突然在社交媒體寫著:「上年,我們分開了,兩個人比從前更了解對方,多了一段糊里糊塗的共同記憶,一場離合散聚的共同體驗,情誼不會結束,而是生命裡多容納一個靈魂。」她清清楚楚記得那天自己為何做了離婚的決定,不過如意料中的,並沒有透露任何細節。外婆知道後也沒說些甚麼:「她基本上完全都不關心。」有天電視正在播一個飲食節目,介紹日本一間和牛餐廳,外婆突然間跟她講:「『阿芝你離婚,不如我們去這裡散心?』正粉腸!她居然公器私用!」現場捧腹大笑。笑罷,阿芝話題又回到婚姻:「其實婚姻是甚麼?婚姻就是結拜兄弟。就係咁咋!斬雞頭撒狗血,以後你就是我兄弟,我是你兄弟。而且這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家人的結合。說是結拜了,那當然要有義氣,但那個義氣不只是你撐我我撐你喎,裡頭還有很多的義務,是不需要對方開口講的,大家互相要有擔當。婚姻當然有義,甚至好大程度是義!」離婚最主因是結婚,但離婚是有意義的,那是一記當頭棒喝。「婚姻有好大部分都是雞毛蒜皮的事,例如我抹地他縮腳;我叫他攞衫去洗他攞衫去洗;喂你去樓下同看更講樓上有人掉嘢啊哦好啊我現在落——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就是婚姻,不是任何一個高度戲劇性的情節或場面。那些東西佔了婚姻九成九的時候,而如果你不認為那些東西值得珍惜的話,那麼婚姻裡邊九成九的時間你都沒有珍惜。」所以愛情有雷,婚姻有義。
離婚後,阿芝人生首次獨自去了一趟冰島旅行,至於為何選擇冰島,倒不是出於任何浪漫意味或末日情感,腦海先不要放出〈雷克雅未克〉的背景音樂。「因為當時冰島要火山爆發,當時全國即將進入緊急狀態。」她大笑道:「真的好好笑,當時我看到好多人就特意去冰島做些超級無厘頭的事,拍了很多短片,如掉隻蛋下熔岩等它爆、放一條熱狗腸烤熟它……當時我在想,那些人咁無聊,我又去!所以就選擇了冰島。」勁無厘頭!不料這個冰島的旅程,會成為她獨腳戲的主線故事:「這是一次超級災難性的bad trip,所以勁好笑。看別人的悲劇就是特別好笑的吧?但在這個旅程中,我反省了許多關於自己的事情,所以這個旅程除了去了冰島,也穿梭在好多不同過去的事件和記憶中,由我十幾歲考DJ的那個自己開始,我在這場騷要不停向過去的自己發律師信,數臭她!質問她!」這場7月中上演的《芝姐災難大全》除了是一個獨腳戲,與以往不同的是它還是一個共同創造的作品,由海報至劇本,背後有一整個團隊籌備,每個人都會交出自己那份想像。

寫劇本其實是猜謎
除了《芝姐災難大全》,阿芝還有一部仍未正式公映的電影《送院途中》,是她事隔足足十年後,再度執導電影,也是她首次自發性地要拍的一部電影。《送院途中》劇本其實早早便寫好,故事的來源正是媒體常常提及的阿芝企圖自殺事件。事源在那件事之後的十年,阿芝開始做棟篤笑,她在生日正日那天搞了一個叫「Happy birthday to me」的演出,有人在她的Facebook留言:好開心你死唔去。好奇心驅使下,阿芝主動向留言者打爛砂盆問到篤,居然意外地重遇當年送她去醫院的救護員。後來她請對方來看騷,對方送了一部救護車的模型給她做生日禮物。看著檯頭的模型,她不禁開始想像,救護車裡頭的人是如何生活。「車裡頭有那麼多的創傷,一天到晚就是爛傷口、爆缸、跳樓、癡呆、老人家……在裡頭工作的人,是如何處理自己的創傷?於是我就開始寫。」
在編劇的身份中,按年資計阿芝是業界前輩。去年她開了一個編劇班,幫助有志寫劇本的人。「100個編劇中,有99個編劇都是在完成第一個劇本之前放棄的。」她續說:「其實我不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編劇叻到可以去教人。但我會教得好,因為我的天賦是消化某些東西,然後再向其他人表達。」她幾年前曾經說過,創作者與創作之間需要有段距離,才會建立到層次。「有時見到差不多年紀的編劇導演,我都會話,喂,你別寫你那些麻甩佬事啦,你去試試寫初戀。」每一個故事的開始,都是開始自許多個未解的謎團。「例如一個角色是好乞人憎的,我就會去思考,為何他這樣乞人憎?為何他要明知無益處都乞人憎?為何這個人不講他乞人憎的理由?是不是不能講的?那甚麼時候先會講?幾時先會爆?想到這些好多謎的人,就會好想寫。」
事隔多年,關於意圖尋死的往事,已經大江東去,阿芝有時還會拿來幽人一默。「幸好天堂拒我於門外,大喊:『X!行返出去啦卓韻芝!』」。想起若干年前她做一個藝術企劃時,用上甚有存在主義意味的題「Born to be witness」。今日,她仍活著,仍在見證,仍與自己的創作死去活來,但她與快樂的距離只相隔一份熱辣辣的Burri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