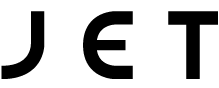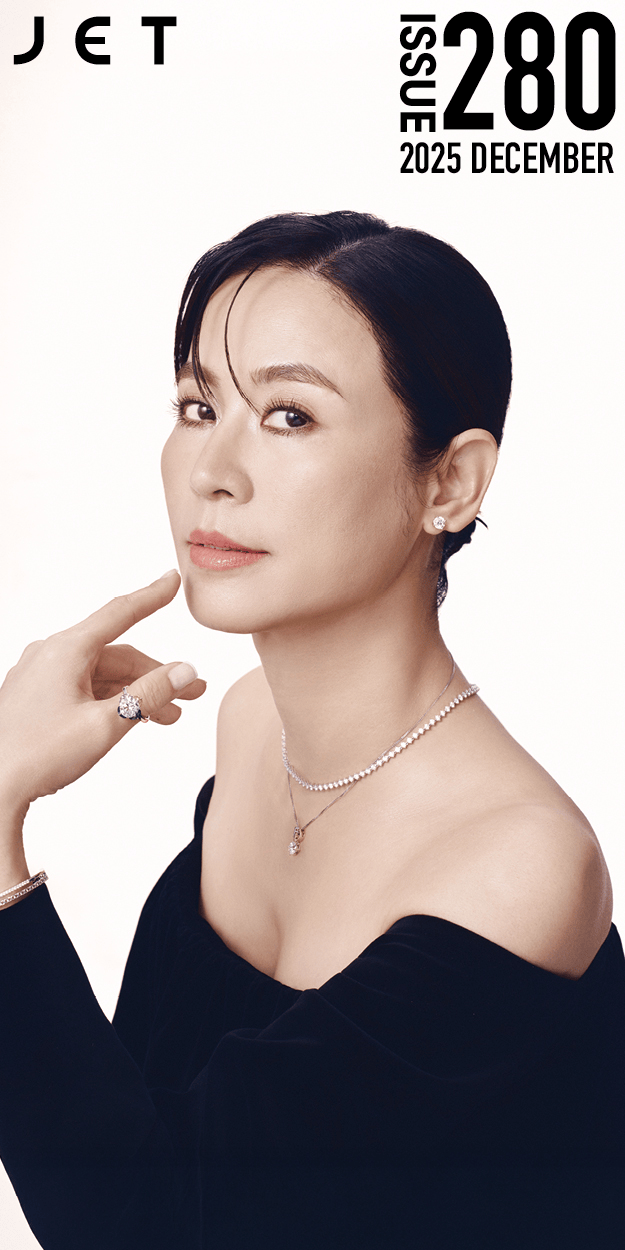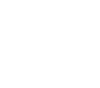在沙漠澆花 杜篤之
2025-04-03

杜篤之第一次來香港大概是30年前,他對香港的第一個關於聲音的印象是交通燈,行人過路時響起急速「篤篤篤篤」的聲響,斷定了他對這個城市的印象。30年後,他由「小杜」搖身「杜哥」、由錄音室助理變成了金馬獎紀錄保持者之一,他人生的聲譜漸漸由單聲軌變成杜比立體聲;早幾年他受邀成為美國電影電視工程師協會年會作講者,是該會史上首位華語講者,怪不得他會被冠以「國寶級」的名銜。但時至今日,杜篤之依然專注華語電影製作。被問到亞洲電影還缺哪些聲音,他反問:「要是把沙漠小花搬到熱帶雨林,花會變成怎麼樣呢?」
text. yui
photo.Hoyin
venue.The Langham, Hong Kong 香港朗廷酒店
special thanks .Asian Film Awards Academy 亞洲電影大獎學院

三天不理楊德昌
杜篤之17歲入行,到4月他便進入古稀之年。今年也是杜篤之入行的第53年,高中畢業後他便進入中影錄音室擔任助理。最初人人都叫他小杜,後來開始有小輩叫他杜哥;叫著叫著,開始連楊德昌、許鞍華等導演們都改口叫杜哥。
導演之中,他與楊德昌、侯孝賢感情甚督,三人識於微時,談起兩位他笑容未減。「好像大家對楊德昌的評論都是關於他的壞脾氣,片場罵人的往事。但在我身上,這些都沒有發生過。」他倒是因為楊德昌在片場發脾氣,而生過對方氣。「我三天沒理他!本來在片場每天見面,我有三天都不願跟他說話。」最後這場冷戰,還是由楊導打破的。杜篤之笑指:「第四天換景的時候,他來敲我車門,問可不可以坐我的車。」對於大名鼎鼎的楊德昌來說,這算是鮮有的低聲下氣。「他就有這樣像孩子的一面,是很可愛的一個人。」
又有一次,他跟楊導大半夜跑到陽明山。「《青梅竹馬》有一場戲,是他拍台北一些老房子,然後他拍的時候用燈去掃過房子,展現房子輪廓。那個燈我們是預設是一台車開過去,很安靜『唰』的一聲照到所有畫面上的房子。有天收工比較早,晚上十點多收工了,我就跟楊德昌兩個人開車到陽明山上,去找哪裡可以錄到這個聲音的地方,在那邊到處走。那我如果在一個地方開車開上坡的話,他們就要加油,車子開過去會不夠安靜。後來我們就找到一個可以下坡,用滑行的方式走,順利呈現走入到一個開闊區域的聲音。」為一個只出現數秒的聲音,他們足足找了一整個晚上。
從楊導第一部作品《一九〇五的冬天》(編劇)作品開始,杜篤之便一直是他的戰友,當時台灣電影正經歷瓶頸期,他們急著挑戰行業裡頭一切常規。「跟他工作以後,大家都想要做一些改變,我們共同做了很多實驗,希望更改產業以前的習慣。每次做了一個新的片子,彼此便會互相分享做了甚麼新嘗試,聊聊還有甚麼可以去試,是一個一起成長的過程。」兩人合作下,也確實立下許多不得了的成就——《恐怖分子》以事後配音的方式擬出同步錄音效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則是首度使用同步錄音技術,以超越台灣水準的技術進行仿真處理。

在打雷,你知道嗎?
另外一位中影戰友是侯孝賢。杜篤之說,這麼多年來唯獨候導始終沒有改掉習慣,一直都是叫他小杜。侯孝賢曾形容杜篤之是個「音痴」,但事實上他自己亦不遑多讓。有天台北打雷打得特別兇,侯導來電劈頭就問:「在打雷,你知道嗎?」杜篤之馬上意會,更笑指自己已經在錄音,兩人的默契不言而喻。杜篤之形容,侯導是一個很敦厚的人,他早早開始當導演,而他當導演的時候,已經有一位固定的錄音師,而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助理。但後來,杜篤之因《海灘的一天》名氣漸大,有一大堆新導演慕名而來,侯導依然沒有找他合作。有次兩人碰上,侯孝賢主動講起這件事。「他說小杜,你知道為甚麼我都沒有找你嗎?因為如果我也找你的話,那個老師傅,就沒有人要找他了。」當時杜篤之依然以助理身份,完善侯導對聲音的要求。
不過要數當中最標誌性的,一定是二人首度合作的《悲情城市》。杜篤之在這部電影以簡陋的設備,土法煉鋼地完成了台灣首部同步錄音的劇情長片,而《悲》侯導在威尼斯影展奪金獅獎後,馬上將獎金換成百萬鉅資的錄音設備贈予杜篤之,是電影史上一段著名佳話。然而與侯導無數的合作中,《千禧萬波》對杜篤之來說真正刻骨銘心,因為他是杜篤之職涯做過最難的作品。「《千禧曼波》開拍之前,侯導就跟我們講,他希望這次拍攝有一點紀錄片的感覺,他每個鏡頭都不作事先綵排,也不試戲,而且只會拍一次。」由於無法事先得知演員走位、行為等,錄音難度瞬間提高,杜篤之生平第一次感到極度挫敗。「拍了將近一個月的東西都是無效的,能用的東西很少。」後來他找來一個多軌錄音機,前期把聲音分開錄製,後期把聲音合起來。「《千禧曼波》之後,台灣電影的現場錄音的工作方式就全部都改變了。我們訓練下一代錄音師的方法,也隨之改變了。以前錄音都是在現場錄好,我們訓練的是要怎麼混入不同聲音,而觀眾不察覺有調整過。但後來有了多軌錄音,就不再訓練他們做這件事了,只訓練他們怎麼樣把麥克風佈局到裡頭,然後把聲音錄回來。」
在遊樂場抓個人配音
杜篤之修讀電機出身的,最初他對音響的興趣遠遠超過電影許多。他對電影聲音設計的熱忱,是從與楊德昌、侯孝賢等新導演的互動當中,慢慢碰撞而來的。當時台灣的錄音技術不精,電影採用事後配音的方式,因此在電影的功能仍未得到重視。而聲音的呈現方式變相古板而單調,電影中的配音一式一樣,男男女女不是字正腔圓的播報員聲音,就是帥哥美女的標準聲音。杜篤之說舊時代的配音員早上永不開工,因為剛睡醒嗓子還未開。「做助手的時候,我就覺得這事情好像怪怪的,不應該是這樣,因為我覺得好像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聲音的特色,不好聽的、沙啞的、洪亮的,都是特色。演早晨的戲,人物嗓子還未開才是正常;一個有不同職業個性的人,聲音也會有不一樣,呈現出不同生活 背景。」
因此,杜篤之與一眾新導演開始大力推動讓演員自己配音,就算是小角色也要找到接近的人物來配音。他記得當時中影錄音室旁有個遊樂場,裡頭阿嬤阿伯甚麼人都有,他常常在那裡抓人進棚配音。發展到後來,杜篤之甚至不再找專業配音員:「我們寧願是帶有口音,講得不好,國語講得不好的人,但是是他自己的聲音。我們寧願用這種方式配音的。」除了人聲,這種求真的精神也拓展到環境聲音,他開始厭倦錄音室只有一種鳥聲的音效。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他開始帶著器材四處錄音。
然而追求真實是過程而非終點。收集到不同聲音,杜篤之又產生新的聯想。「既然我們可以控制,那我們為甚麼不把它控制得更像電影該發生的狀態?」他開始把音效視為一種說故事的方式,而不只是輔助畫面。「所以後來我們就再去尋找,看我們還有甚麼東西是我們現在電影裡面聲音呈現的東西,有甚麼是多餘的,甚麼是不足的,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把電影中的聲音去蕪存菁。「呈現出來的不只是真實,在這個真實底下,還要有電影感。」譬如說《大佛普拉斯》的結尾,大佛裡頭慢慢傳出敲打聲音。「我要引導觀眾發現這是一個求救訊號,有一個人被封在裡面,然後在那個場所她醒了,她在求救,那我們想做這個。所以那個敲打的節奏是非自然的,不是機械式的,她已經沒有力氣了。」

如沙漠的花搬到熱帶雨林
荷里活電影圈早幾年爆發罷工運動,AI人工智慧的威脅是其中一項抗議重點。AI工具的運用至今尚有巨大的爭議,有電影人認為AI會剝奪電影產業的創作活力與多元化,也有電影人活用AI把演員回春或修改口音。杜篤之認同罷工中提及的智慧財產(知識產權)問題需要重視,但對於AI對電影創作的影響,卻有所保留。「AI對我的工作沒有影響,除非它造成侵權的問題,我覺得不需要去抗議。」他指AI只是一個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為「抗議」而重返複雜方法並不合理。他認為人們應該要趕快去理解這種新技術,而非馬上拒絕並轉身離開。「它現在還不是很完美,因為它還很年輕。 但你怎麼知道哪天會得長比你大?所以你要趕快接受這個新的東西,要知道怎麼運用它。」
杜篤之表示,以前要消除音軌的雜音,要靠耳朵去找這個雜音的頻率,再用傳統的工具把頻率去除;現在AI工具只消一秒就可以找到那個頻率,縮短大量工作時間。「今時今日要訓練一個新人靠聽覺去找到那個東西,是要訓練很久的,耗費非常龐大放的訓練成本。就算訓練好,如何判斷仍是一個變量,又是另外一個成本。然後時間又是成本。」授人以漁,也要考慮是甚麼「漁」,而如何按情況使用不同工具,也有一套智慧。杜篤之與AI相處之道,其實也是一種「用人為才」。該不該運用AI無關於創作內容的問題,而是創作心態的問題。
亞洲電影近年在國際舞台一爭長短,香港也有作品漸漸走出舒適圈,吸引其他國家影迷。這些沒好畫面偶然讓人錯覺香港的文化價值回暖,但眼見本地戲院一間一間結業,似乎仍未可以樂觀面對。「如果是一朵花,這朵花如果長在熱帶雨林,它會長很大一朵,但是這朵花如果長在沙漠,它是長得的小小的,因為它養分不夠。但是你說沙漠那朵花比較漂亮,還是熱帶雨林那朵比較漂亮呢?只是花的形狀不一樣,但是都漂亮。」本來只問杜篤之對亞洲與荷里活製作的看法,不料意外呼應本地電影產業的現況。「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養份,我們可能長著小花,但是我們的小花也很漂亮。要是你把小花一夕之間搬到熱帶雨林,它可能會被雨水淹死;如果花需要大量水份才能長大成那種狀態,把它移植到沙漠,可能就枯萎了。所以哪樣的花也需要適應生態環境來生存、來成長。」他續說:「重點是,就算都是長在沙漠裡面的花,有的會開得比較大,有的開的比較小,那就是適應生態的 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