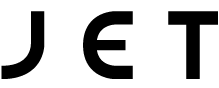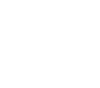黃詠詩專訪|與黃子華許冠文有緣 《破地獄與白菊花》第十一度公演
2025-05-02

黃子華是神,他有能力讓香港人一呼百應,《破地獄》電影無限破紀錄,《香港式離婚》58場舞台演出一票難求。也許沒太多人知道,《香港式離婚》出自黃詠詩的手筆,十多年前成功獲得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同樣有趣是,她很早與黃子華及「破地獄」有緣,卻不是對方主演的那部電影。
出身於道教家族的黃詠詩,早於2008年自編自演的獨腳戲《破地獄與白菊花》,令她首次獲封「劇后」(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喜/鬧劇)),自此十七年來已有十次公演,每次她都會在舞台上「破地獄」,更邀請觀眾與她上台一起「破」。「那段戲是最興奮的,上台那個人一定會甩,全世界一起看著他甩,我就負責執,然後我們一起甩,一起笑到尾。」
《破地獄與白菊花》的起點來自真人真事,2006年祖母離世,成長期間受天主教教育的黃詠詩,被逼要見證一場世紀打齋,她本來想嘲笑那些「無謂」的儀式,後來卻發現自己被感動。事實上,不只是黃詠詩一個被感動,還有千千萬萬的觀眾,否則不會演極都有,幾乎成為了不少劇迷春秋二祭的傳統儀式。
適逢去年《破地獄》票房大賣,今個月更將推出電影加長版,加上《香港式離婚》月前大賣,但原來又是黃子華鼓勵黃詠詩重演《破地獄與白菊花》,此時此刻準備第十一次公演,可說是電影加長版以外的完美番外篇。
如果《香港式離婚》和《破地獄與白菊花》要二選一的話,好難回答,他們是同一年寫。《香港式離婚》要與很多人合作及溝通,《破地獄與白菊花》不同,我自己著黑色旗袍拖喼在街邊演出也可以,好自由。二選一來說,現在我會選《破地獄與白菊花》,因為夠自由。
黃詠詩
text. Nic Wong|interview. 金成、Nic Wong|photo. Oi Yan Chan|makeup.Tiffany Fong@TF Brow|hair.Jaden.R

黃子華送喉糖
黃詠詩的作品不少,最早為公眾熟悉,大家卻未必想起原來是電影。2004年,她與彭浩翔合寫《公主復仇記》劇本,榮獲金紫荊獎最佳編劇及提名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其後2008年自編自演《破地獄與白菊花》及2010年《香港式離婚》,後兩者相隔十多年,依然長演長有。
黃詠詩早已與《破地獄》有緣,難以想到早於二十年前,黃詠詩已經與「Hello文」許冠文合作,為他的《05鬼馬TALKSHOW》擔任編劇。「那次是梁榮忠找我幫忙,當年他幫手做很多talk show,想找個年輕女編劇幫許冠文一起構思,提供多一個角度,於是認識了Michael。與他合作很舒服,他其實一早已經預備好,當時每日都在聽他年輕時的精彩故事,每次開會我都很開心。」黃詠詩主要幫忙為talk show定下骨幹,讓前輩知道怎樣分布重點及力量。「後來有日他的公子告訴我,Michael覺得我成功將那些故事捆綁一起成為了那條脊骨,更有信心地演說。其實我最大的功勞是,幫手做了他的第一個聽眾吧。」
至於「道生」黃子華說過,《香港式離婚》是他心目中的三大經典之一,原來他與黃詠詩更是好友。「記得《破地獄與白菊花》第二次還是第三次公演時,子華剛剛排練另一個舞台劇,那個劇的導演從小看著我大,我託他叫子華來看我的solo,結果真的來看了。」黃詠詩深深記得,當時表演場地只有一百幾十人,對方看完走進後台與她見面。「子華走入後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一包喉糖給我。他說我居然不停高速地講足一個半小時,所以想請我吃一粒喉糖。」黃子華的確窩心,也的確有趣,自此就與黃詠詩結下友誼。「很有趣是,我們只是間中聯絡一下,但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決定,我好久都不找他,但當我問他的時候,他真的很誠懇地用個人經驗來回答我,又會跟我談得很久;他又不是喝很多酒,但他又喜歡請我喝酒,十幾年來我們就這樣認識大家,直至他演《破地獄》那部電影時,我笑說他終於做我這一行的事了,很有趣。」
黃詠詩認為,《破地獄》電影講述人的故事,以及關於死亡的故事,而《破地獄與白菊花》則集中火力講述儀式。劇目於2008年首演,真人真事改編,黃詠詩自小在道教打齋家族長大,但八歲因父母離異,她跟隨基督教徒的母親,以及就讀天主教英文中學長大,直至2006年祖母離世,當時年約三十歲的她見證了一場世紀打齋。「我原本想做一個作品,嘲笑那些無謂的傳統儀式,因為過程中有很多笑料,尤其我認為人死了就死了,如果愛一個人,好應該在他生前做嘛,為何人死了才喊苦喊忽呢?」她一心想反抗家族意識及傳統,怎知道她與叔叔開始這方面研究時,卻發現那種愛的表達是這樣深厚。
我記得那時導演李鎮洲先生鼓勵我將真實過程寫出來,我原本想笑,怎料被那些事情感動了。現在人們趕時間,總不明白為何要拿著一支香站著十五分鐘?也不明白為何要圍著走來走去?無端端捉那個長子出街,不知道做甚麼後又回來了?人們覺得,那些儀式好像呆坐那裡等時間過去,卻不知道自己錯過了甚麼?傳統中國人不懂說愛你,但其實每個儀式都是愛……
黃詠詩

破地獄笑料
還以為黃詠詩的內心,自小上演著一場宗教之間的角力,結果並非如此。「在我的世界是並存的,我一直以為天主教『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及聖靈,就是我小時候家中所拜的『三清』,只不過是他們的名字不同。後來我與道教的緣分斷了,家中父母離婚,我跟隨了媽媽,那邊是基督教,我讀《聖經》由三歲讀到二十歲,中六中七還要考試,了解《聖經》比道教經籍更為熟悉,卻不覺得有衝突。」她強調自己不是教徒,沒有受洗,卻在羅馬天主教學校德雅中學長大,對宗教信仰的想法比較開放。「天主教有很多音樂、風琴樂器,儀式很乾淨,但道教的喪禮比較大鑼大鼓,又有很多動作、功架及傳統,只以為是中西之分。」
長大後,黃詠詩繼續開放,就將兩者融合。「道教那邊有很多可見的儀式,譬如求聖杯問yes or no,就像哈利波特有符咒符水,都是你求助後即時有答案的東西,但相對沒有甚麼談話的;天主教卻是團契,教徒一起讀《聖經》學道理,有些道理很好,好像撒種子的比喻,又教你做人要靈巧如蛇,純良如鴿子,像白鴿那麼純,也一定要靈巧。這些字是從小到大都在影響我,並不是人家說了道理就要聽,人要靈巧,真的太不同了。」
「不過,我覺得除了聊天講道理之外,有些儀式是很重要的。我覺得道教的天人合一,你裝了一注香和上天許願,其實就是和自己許願。上天就是時間,時間會幫你處理這些事,但這一刻你一定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甚麼。所以,你去裝香許願的時候,稟報是一個重要的儀式,而在一個時間的機緣上,正視這個問題,而那件事我們身邊的人全部聽不到,就算是幫你的師傅,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喃喃自語說甚麼,但這一步很重要。天主教每日都會叫你祈禱,道教弟子每日都會裝香在師公身邊和師公說話,但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會日日跟天地祈禱說話,所以我今日做這件事遇到障礙,我們未理解到是甚麼,但請求上天指引,其實就是讓時間去處理。」
就如《香港式離婚》都等了十五年才得到今日,過程間我還不停重演,重演到今日才終於得到一個這麼大型的情況,但當中都過了十五年。你不可以昨日寫劇本,今日就說我要得到這樣嘛!
黃詠詩

因為義氣,所以留低
《香港式離婚》是2010年的作品,黃詠詩當時只有三十多歲,還未結婚及未有小孩,她只是以一個孩子在年少遇上父母離婚的角度出發寫劇本。現在回想小時候的家庭離異,黃詠詩承認有影響,但不算是陰影。「有人形容為創傷,但我會形容為人格的一些特色及weathering(變形褪色),你必須要擁抱它,同時令你早熟,太早就要變成一個大人。」那時她很早就要幫忙照顧妹妹,當同學們有課外活動時,她就要回家煮飯,很早就要憂柴憂米。「好處是,到現在仍然很想玩,還未玩夠,因為我小時候不能玩。」小時候不明白父母為何會分開,長大後更覺得他們很勇敢。「當時沒有人會離婚,我會很欣賞父母真的勇於抉擇,自己的所愛不是這個人,尤其當時他們年紀也小,處理兩個小孩時可能沒有現在那麼多資訊來交代,所以引致一些壓力。」
創作《番》的時候,黃詠詩正值面對著一段長關係,可惜最後還是要分開。「很多人都覺得要珍惜長關係,好像投放了很多時間,但我覺得時間不是這樣計算,時間不是一個長短的問題,而是你和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所發生的事對你的滋養及個人有否進步?每個人的case都不同,我之所以保持這麼長的關係,很大原因是我的義氣。」她坦言,那段長關係當中,對方是個癌症病人,病情持續十年反覆地康復又復發。「我一直在他的身邊,病情嚴重到要換骨髓,康復後隔了兩年又復發,後來我們發現真的性格不合,還是決定放過大家,再找另一個100%愛自己的人。」
回想當時,她自言需要尋求一些關於長期病患者照顧者的協助,因為壓力很大。「那時我不想離開及放棄對方,但當我由少女去到中女的時候,我真的想到還要繼續嗎?我的階段不同了,當然要放棄十幾年的長關係很可惜,但我還要為我之後三四十年好好準備。當一個女人要離開的時候可以很絕情,我一個電郵便和他分手了。」再度回想,她深感當時的處理方式也不好,沒有好好解釋為甚麼想走,但她的直覺就是,是時候分開了。
於是,《香港式離婚》就是從由離婚開始說起。「當你想在婚姻中離開的時候,法官根本不會理會誰人有染,誰人先有離心,他只會判定你們決定了沒有,一旦決定了,就是分配男女雙方剩下的資產,包括可見的物質上糾纏,例如金錢、孩子等等,他就是處理這些事。透過這些方面證實彼此相愛過,其實是很絕情的。」事實上,當兩個人分開的時候,唯一可以證明的,正正是這些功利而實質的東西。「從那個絕情再說友情,正是《香港式離婚》最大的動力。」


離婚前的激情對話
時至今日,結婚生女後再看《香港式離婚》,主角換上黃子華及劉嘉玲,規模更大,黃詠詩反而慶幸自己當年對於婚姻尚有希望的時候寫了《香港式離婚》。「因為真正面對離婚時,其實已經沒有話題,雙方已經是仇人,已經dry到沒有東西可以互相分擔,根本不會有激情對話。尚有激情對話,其實還有得救,因為你還想和他解決。最沒有得救的就是冷漠。」她今次再改寫劇本,認為劇中兩人只要離開了婚姻這個設定,其實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回頭看這段婚姻,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令兩個這麼聰明、這麼懂得表達的人,一到了婚姻,卻發生了問題?只要他們說了分開後,就開始甚麼都可以說了。我就是想這樣設計的。」劇組們原來真的收到一些《香港式離婚》的觀後感,反映有觀眾本來與丈夫快要離婚了,但看完真的坐下來談了一趟,決定再試一次。「58場共有五萬多觀眾,就算救到一單,我們都做了功德吧。」
想當日,原來是《破地獄與白菊花》的排練是直接影響《香港式離婚》的出現,因為黃詠詩激怒了李鎮洲導演。「那次我在房間裡,問他我演得如何,他不作聲,我叫他給反應,他睜大眼睛,怒吼:『從來只有我叫演員給反應。沒有演員叫導演給反應。』接著他不睬我兩個星期,我覺得這個人很陌生,很害怕,成為了我想寫《香港式離婚》男主角CK的重要精華。」今趟重演《破地獄與白菊花》,卻又因為《香港式離婚》中扮演CK的黃子華。「這次是子華鼓勵我重演,那個期來得很急,我跟他說,每一次都要思考是甚麼觀眾進來看這一個劇。現在很幸運的是《破地獄》電影很受歡迎,它講述了很多感情,很多不同人的小故事。反而儀式方面沒有太多說話,但它拍得很美的,因此儀式上我可以補足,現場看的話,力量很強。」
如果你看過電影,這麼禁忌的題材都有這麼多人入場看完又看,其實是很好的。證明這個題材很多人都未看過,又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證明,這個作品是集中講儀式的禁忌,更能滿足觀眾對這件事的好奇……
黃詠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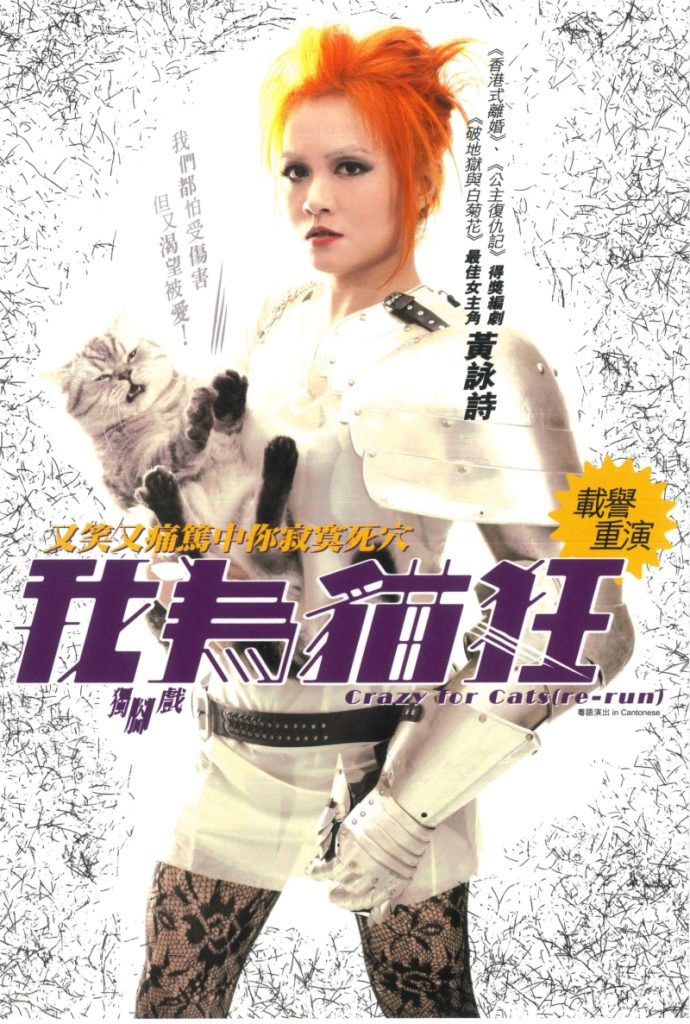

白菊花之任務
黃詠詩坦言,最初三十幾歲演出時,頭半節全部都是講那些在靈堂做錯事的儀式。「記得最初兩年演出,上半場笑到嘔,但一到下半場,就感覺到觀眾聽到嚴肅東西時,就開始向後退;後來演出的分水嶺是,有一年我在十月演出,那年香港發生了一個南丫島沉船事件,當時形容為海難,我的尾場演出那天正值事件的頭七。那個星期的演出,突然間好像上到急流,頭半節繼續笑,來到後面講嚴肅的部分,你感覺到那個悲傷是撐得住全場的,因為那個悲傷都在大家的心裡面,笑完之後散發那種悲傷出來,自此這個演出開始提升了一個層次。」
隨年月過去,黃詠詩不想經常遇上那麼多悲痛的災難,但她明白了生離死別是甚麼。包括身邊有朋友突然離開,亦包括具標誌性的社會人物離開了大家。「他們代表了我的青春,那些東西離開後,我真的要靠自己來面對和支撐。我一定會好好記住,他們的實體已經不在,但我一定要記住他們的精神,因為他們每一個出現過的人、精神,都是我的一部分,所以那個重量隨著我的年紀增長和骨骼疏鬆,都會撐在演出裡面。」
總括來說,黃詠詩坦言自己性格古怪,但她深信:「一個人有些古怪的性格,一定是有任務的,否則上天不會給你一個這樣的敏感度去觀察這個世界。上天要你經歷痛苦之後重生,經歷過後,你就懂得看到需要這種幫助的人,從而告訴他們:『你不孤單,我明白的,我幫你走這段路。』」她想通了,也就沒再黐線了。「如果我沒有創作這一行,我早已發神經黐線了,以及為身邊的人帶來無窮災難。我覺得表演是研究人的行為,編劇是編排每個人的命運,我將我過度敏感的部分超越現實的材料,安樂地放在規劃了的世界,我在這一行做了二十多年,我有足夠的經驗和技術去編排這些東西。」現在,她明白每一刻都在學習,編排的過程令她搞清楚很多理不清的現實。「現實是無常的,你一出到去,就不知道對方說甚麼,但在戲劇世界中,你可以精煉無常,成為了我知道對方為甚麼這樣說。我知道你為甚麼會有這樣反應。所以,我在這裡得到安定。」
我有創作的能力,上天賜給我,我就要做這個服務,服務大家,我知道怎樣說這個故事。你們來看這個故事。你們不用看我,看這個故事就可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黃詠詩

黃詠詩簡歷
1976年出生,香港舞台劇編劇及演員。出身自道教家族,8歲時父母離異後隨母親成長及幫忙照顧妹妹,中學就讀於天主教顯主女修會創辦的德雅女子中學,其後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
學院,後再獲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碩士,主修編劇。
2002年起為香港不同劇團任編劇,早年曾為森美小儀歌劇團編寫《亞卡比槍擊事件》劇本,亦擔任過《許冠文05鬼馬TALKSHOW》編劇。2004年憑《公主復仇記》電影劇本,榮獲第10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編劇獎及第42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提名,其後改寫為舞台劇《公主復仇記》,由黃詠詩、梁祖堯及彭秀慧主演。
黃詠詩曾多次獲香港舞台劇獎提名及得獎,其中2008年獨腳戲《破地獄與白菊花》便首獲第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喜劇/鬧劇),2011年《香港式離婚》獲得第二十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2020年憑《三生三世愛情餘味》獲得第二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填詞。
黃詠詩多年來獨腳戲作品《我為貓狂》及《胎Story》等,亦有編寫過《賈寶玉》、《寒武紀與威士忌》《三國》等,去年《香港式離婚》獲黃子華讚賞被重演連開58場;其獨腳戲成名作《破地獄與白菊花》則於今年5月第十一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