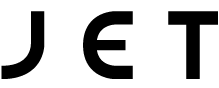PEOPLE
SHOWBIZ
《雙囍》余香凝、田啟文專訪|香港「父女檔」勇闖台灣電影演出!連擺兩次婚禮真有其事?
台灣電影《雙囍》賀歲不久,接力來到香港上映。雖然是台灣電影,但片中亦有兩位香港代表在陣,分別是曾經憑《緣路山旮旯》及《白日之下》入圍金馬獎的余香凝,以及邊拍電影邊觀摩彼岸電影生態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二人在電影中演活一對父女,既有深情演繹,亦提供廣東話及港普對白,在兩場繃緊的婚禮之下,提…
《多麼好》|粉紅A專訪 為城市獻上粉紅色
必須承認,2019年單曲循環著〈若世界在明日結束〉的時候,未料到粉紅A會重新活躍起來。作為九十年代末至二千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獨立樂隊,粉紅A自1998年發表首支樂曲〈陳愛男〉,就好像為樂隊的風格奠下了粉紅色的基調。樂曲大量曖昧、情色、身體感的題材,居中寫小人物也寫大社會,寫法玩味又有點知性,又鹹濕又…
《夜王》|「歡哥」黃子華、「V姐」鄭秀文專訪:拍電影似用心追女仔 原來Tom Cruise才是終極夜王?
《夜王》終於登場,黃子華、鄭秀文聯手陪香港人賀歲!子華神繼3年前《毒舌大狀》與吳煒倫導演再度合作賀歲,今次他自言化身面對現實的韋小寶,不去服侍乾陸帝康熙帝,反而留在尖東夜總會服侍一班大帝,哼唱「可以笑的話不會哭」。Sammi則首度與Jack導合作,她享受被導演調教,同時也努力令V姐角色更立體更有層次…
《夜王》專訪|Renci楊偲泳、Mandy譚旻萱、Hazel林熙彤、Sumling李芯駖、Laiying鄧麗英:嫵媚迷人的夜場故事
萬眾期待的賀歲片《夜王》終於來臨,除了黃子華、鄭秀文神級主演外,戲中有一連串目不瑕給的性感女角,在電影中的夜總會場景中嫵媚迷人。香港近年少見夜場主題的影視作品,一眾女角雖未踏足過昔日繁華的尖東夜總會,但她們與夜總會工作的小姐們分享後,今次踏出舒適區,無懼性感尺度,希望展現自己不一樣的面向,說好夜場女…
農曆新年情人節Final Call|Kimpton HK 尖沙咀金普頓酒店一系列團圓優惠共享佳節喜悅
農曆新年及情人節將至,準備好度過難忘佳節沒有?香港尖沙咀金普頓酒店(Kimpton Tsim Sha Tsui Hong Kong)新開不久,是時候把握酒店的首年佳節,與伴侶家人一起過,締造前所未有的節日氣氛。酒店先於2月12至14日呈獻精緻情人節餐單、雞尾酒與瀰漫浪漫儀式感的套房優惠,以味蕾牽動情…
梁小龍、陳觀泰專訪|卅年後《打擂台》再遇 學武比人多四件武器更要克制 武術最難搵人虛位
***訪問刊於2010年6月號,《JET》雜誌第94期*** 郭子健找梁小龍和陳觀泰來拍功夫戲,適合到不得了。 因為他們到今天依然熱愛功夫。見微知著,陳觀泰卡片上的名銜雖是「監製/導演」,但隸屬的卻是「大聖劈掛門電影工作室」;梁小龍的更厲害,卡片上除了有自己簽名,還簽了當年演得紅極一時的「陳真」名字…
渣馬跑手訪問|Carina@VIVA、Madboii、Hayson Kwok 三個歌手同一份信念:明明跑步好辛苦,但依然選擇堅持
女團VIVA隊長Carina、創作歌手Madboii及生力軍歌手Hayson Kwok,今年多了一個身分,就是渣打香港馬拉松10公里賽事跑手,有著不同時間目標,但信念一致。他們加入“FOURPOINTZERO 4.0“ Nike Running Team後更脫胎換骨,以前有人跑到暈,今日跑步不嫌悶;…
FASHION
THE FUTURE ROCKS 見證每刻閃耀珍貴
如果心動需要一枚閃耀信物來認證,情人節的浪漫便有了具象的模樣。國際培育鑽石創新先驅THE FUTURE ROCKS始終堅信,珠寶是情感的無聲敘事者,以尖端科技淬煉自然本真,以永續理念承載純粹心意,讓每件作品成為日常穿戴與節慶贈禮的理想之選。這次,品牌重磅聚焦Essence系列新作Pavé Cord …
美不求永恆,只求此刻綻放 — Boucheron
Boucheron於首爾揭幕2025年全新Carte Blanche系列——Impermanence高級珠寶。系列由28件精緻作品組成,靈感源自日本花道(ikebana)與侘寂哲學(wabi-sabi),透過光與影、盛放與凋零的對比,捕捉大自然稍縱即逝的瞬間之美。創意總監Claire Choisne…
張敬軒漫步CHANEL花田 法國南部香水之旅
法國南部格拉斯(Grasse),是聞名的香水之都,是CHANEL傳奇香水N°5的誕生之地。從香港到格拉斯,CHANEL N°5香水收藏家張敬軒跟隨CHANEL調香的優雅步伐,在花田間,欣賞星辰之花茉莉的脫俗芬芳,學習採花者的靈巧技術;在工場內,認識萃取香氣的奇妙過程,更與CHANEL專屬調香師Oli…
共賞月相映照之時:全新TUDOR 1926 Luna登場
明月映照之下,眼前萬物從此變成星斗璀璨的美景,喻意美好時刻的來臨。帝舵表藉著美妙的團圓時刻,破天荒地帶來了首款配備月相功能的全新之作TUDOR 1926 Luna,創造出圓月互相輝映的動人景致,為大家送上祝福。今回的誠意之作,品牌更邀請了一位重量級嘉賓參與創作,令TUDOR 1926 Luna再添一…
訪問agnès b.創辦人Agnès Troublé:為生活而設計的衣服
創立於1975年的法國品牌agnès b.,今年剛好踏入50週年。創辦人Agnès Troublé從來不向潮流妥協,不少經典作品即使經過了半世紀的洗禮,仍然讓人津津樂道。我們早前有幸在品牌巴黎總部訪問創辦人Agnès,向大家分享她對香港的印象,以及她的創作思維。 Text: Calvin Wong …
璀璨裡連繫真摯與愛:從Leo Diamond發掘自信之美
自愛的力量,賦予了女生散發不一樣的自信魅力,成為自身的閃耀光芒。 成長路上,每位女性都在時光的淬鍊中積累智慧。母親的教誨如同珍貴的禮物,在我們心中埋下自愛的種子。隨著歲月流轉,我們學會欣賞自己的獨特,讓這顆種子茁壯成長,最終綻放出自信的光芒——既溫暖他人,也照亮自己。 正如Zelia鍾浠文從生命歷程…
LIFESTYLE
農曆新年情人節Final Call|Kimpton HK 尖沙咀金普頓酒店一系列團圓優惠共享佳節喜悅
農曆新年及情人節將至,準備好度過難忘佳節沒有?香港尖沙咀金普頓酒店(Kimpton Tsim Sha Tsui Hong Kong)新開不久,是時候把握酒店的首年佳節,與伴侶家人一起過,締造前所未有的節日氣氛。酒店先於2月12至14日呈獻精緻情人節餐單、雞尾酒與瀰漫浪漫儀式感的套房優惠,以味蕾牽動情…
新春禮盒推介2026 為馬年開一個好頭(不斷更新)
為嶄新馬年注入奔騰氣象! 隨著2026甲午馬年的腳步將近,正是時候以一份別出心裁的新春賀禮,為自己與珍視之人開啟活力滿載、奮發向前的一年。無論是寓意「馬到成功」的吉祥佳品,或是結合當代設計與傳統寓意的精緻好物,一份得體的禮物不僅能傳遞深厚祝福,更能為新的一年賦能鼓勁。本文精選多款匠心獨運的…
Chef Richard Ekkebus專訪|置地文華東方酒店三星餐廳Amber行政總廚:廿年磨一劍 You are what you eat
經歷連續16年獲頒發米芝蓮二星評級,2025年3月,中環置地文華東方酒店內的Amber終於迎來首個米芝蓮三星榮譽及可持續發展的「綠星」評級嘉許,榮獲堪稱餐飲業界最崇高的榮譽,身兼行政總廚及酒店餐飲總監的Richard Ekkebus當然功不可沒。 這位來自荷蘭的名廚,在歐洲訓練廚藝技法,再紮根香港開…
一本鰻利!94年日本名古屋鰻魚老字號「うなぎ四代目菊川」來港再開舖!K11 MUSEA分店坐擁維港海景兼新設專屬酒吧Bar YON
逾90年歷史的日本名古屋鰻魚批發老字號「うなぎ四代目菊川」,曾獲米芝蓮餐盤推薦美譽,去年進軍香港落戶銅鑼灣利園一期,今年繼續擴展香港市場,第二分店於尖沙咀K11 MUSEA開幕,更進一步升級至奢華藝術氛圍,坐擁維多利亞港絕美海景及首設專屬酒吧「Bar YON」,打造視覺、味覺與靈魂的多重饗宴。 來到…
歷來最強按摩椅?OSIM結合世界按摩大師 uDream.AI全球首創五感沉浸式按摩體驗
按摩椅絕非新鮮事,OSIM歷來推出過不少作品,今次全新推出uDream.AI,號稱品牌歷來最具突破性的作品,與新加坡、日本及泰國的世界級按摩大師合作,並攜手聯乘Devialet及Tea WG等及專利 AI 養生科技,打造全球首創5感沉浸式按摩體驗。 uDream.AI憑藉獨有頂尖按摩工程專利技術,成…
回到破格創作的未來:Mercedes-Benz聯乘Offgod:Tate之CLA協奏曲
這款Mercedes-Benz CLA令汽車變成為藝術創作的載體,為當代藝術打開了全新的創作視野、美學觀感。
渣馬跑手訪問|Carina@VIVA、Madboii、Hayson Kwok 三個歌手同一份信念:明明跑步好辛苦,但依然選擇堅持
女團VIVA隊長Carina、創作歌手Madboii及生力軍歌手Hayson Kwok,今年多了一個身分,就是渣打香港馬拉松10公里賽事跑手,有著不同時間目標,但信念一致。他們加入“FOURPOINTZERO 4.0“ Nike Running Team後更脫胎換骨,以前有人跑到暈,今日跑步不嫌悶;…